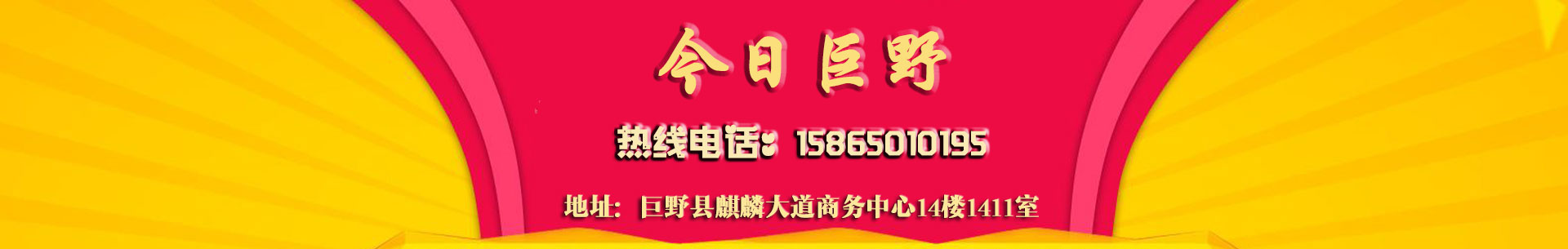八千年回眸與凝望
來源: 作者:張海江 時間:2022-12-12
磁山文化有著八千年悠久文明史,它的發現引起了國內外專家、學者關注。
磁山文化遺址位于太行山東麓,河北省武安市磁山二街村東南一公里的臺地上,總面積十四萬平方米,分上下(即早晚)兩個文化層。它的年代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用碳—14測定的數據距今8000多年。這個遺址的發現,填補了我國新石器時代研究的空白,是我國北方重要原始文化類型。磁山文化真實記錄了八千年前磁山先民勞動、生產情景。其文明進步的發展程度舉世罕見,為研究原始氣候、環境、生產、生活方式等眾多學術問題提供了大量的史料。磁山文化對遠古社會經濟發展研究價值頗高,因此被中國社會科學院命名為“磁山文化”。1988年,磁山文化遺址升級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磁山文化于1972年被發現后,經考古工作者多次科學地挖掘,揭露面積約七千多平方米。遺址中發現了貯存糧食的窖穴及腐爛的粟谷。出土文物5000余件,其中有石、骨、蚌、陶器和祭祀品, 有二十三種動物骨骸和植物種子標本等,還有用于農業生產的石斧、石鏟、石鐮,加工糧食的石磨盤、石磨棒、漁豬工具網梭、骨鏃、箭頭,魚鰾等,還出土了豬、狗、雞等家畜、家禽遺骸。出土文 物有以鳥頭形支腳和大口直腹平底盂為代表的陶器群,有短足的石磨盤和圓柱狀的石磨棒為代表的石器群,其中打制和打磨兼制的比較多,體現了磁山文化面貌是原始的。粟的出土其規模之大,數量之多,實屬罕見,種植粟作物已成為當時先民最主要的食物來源之一。粟遺物的發現修正了國際專家認為粟起源于埃及印度的論點,把我國植粟年代上溯了二千年。在出土文物中,黍、粟的種植、家雞的養殖、核桃的栽培、陶器的制作堪稱世界之最。這充分說明早在八千年前,我們祖先就已經從事農業生產,飼養家畜、家禽,但也經常從事漁獵、采集等活動,過著定居生活。
磁山文化遺址,它在古城武安,與武安輝煌的歷史融合在一起,是它更湮久的組成部分。與現今基礎工業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磁山以農業、氣象、制歷、釀酒、玉石、冶鐵等早慧于中華歷史。
磁山文化博物館所展示的文物令我們的震撼卻是巨大的。相對于安陽殷墟的精致奢華,它質樸的就像八千年前居住在此地的先民們庸常而朝氣的生活。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真不敢相信,眼前這些稚氣十足的陶制酒具就是八千年前的磁山先民們用過的東西;如果不是新眼所見,我也不敢相信那些精美的骨針、實用與審美高度統一、極其配套的陶制鳥頭型支腳和大口直腹平底盂也是八千年前的東西,還有谷物脫殼用的鞋底狀的石磨盤、圓柱狀的石磨棒(像極了我們現在的搟面杖),還有眾多繩紋陶制盛器,就是先民們手工捏就鍛燒磨制而成的。
磁山文化于1972年被發現后,經考古工作者多次科學地挖掘,揭露面積約七千多平方米。遺址中發現了貯存糧食的窖穴及腐爛的粟谷。出土文物5000余件,其中有石、骨、蚌、陶器和祭祀品,有二十三種動物骨骸和植物種子標本等,還有用于農業生產的石斧、石鏟、石鐮,加工糧食的石磨盤、石磨棒、漁豬工具網梭、骨鏃、箭頭,魚鰾等,還出土了豬、狗、雞等家畜、家禽遺骸。出土文物有以鳥頭形支腳和大口直腹平底盂為代表的陶器群,有短足的石磨盤和圓柱狀的石磨棒為代表的石器群,其中打制和打磨兼制的比較多,體現了磁山文化面貌是原始的。粟的出土其規模之大,數量之多,實屬罕見,種植粟作物已成為當時先民最主要的食物來源之一。粟遺物的發現修正了國際專家認為粟起源于埃及印度的論點,把我國植粟年代上溯了二千年。在出土文物中,黍、粟的種植、家雞的養殖、核桃的栽培、陶器的制作堪稱世界之最。這充分說明早在八千年前,我們祖先就已經從事農業生產,飼養家畜、家禽,但也經常從事漁獵、采集等活動,過著定居生活。
磁山文化遺址,它在古城武安,與武安輝煌的歷史融合在一起,是它更湮久的組成部分。與現今基礎工業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磁山以農業、氣象、制歷、釀酒、玉石、冶鐵等早慧于中華歷史。
磁山文化博物館所展示的文物令我們的震撼卻是巨大的。相對于安陽殷墟的精致奢華,它質樸的就像八千年前居住在此地的先民們庸常而朝氣的生活。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真不敢相信,眼前這些稚氣十足的陶制酒具就是八千年前的磁山先民們用過的東西;如果不是新眼所見,我也不敢相信那些精美的骨針、實用與審美高度統一、極其配套的陶制鳥頭型支腳和大口直腹平底盂也是八千年前的東西,還有谷物脫殼用的鞋底狀的石磨盤、圓柱狀的石磨棒(像極了我們現在的搟面杖),還有眾多繩紋陶制盛器,就是先民們手工捏就鍛燒磨制而成的。
我想磁山時期的人們是比較富裕的,糧食有了剩余,才可能造酒。酒從來就是奢侈品,在溫飽不能為繼的情況下,人們不可能分出一粒糧食來供給他人或挪做他用。在人類的黃金時代,他們保持著旺盛的生活熱情和不盡的創造力,他們和諧而純然地與自然相處,于是他們學會了釀酒,他們試著馴養雞、狗、豬等后來我們稱作家畜的動物,大面積種植栽培一種叫粟的作物,而且他們還學會了用植物纖維織布。當地球上的大多數人裸露著瘦骨嶙峋的軀體、饑腸轆轆地采集野果、過著與虎豺相搏、生命隨時都有被野獸吞噬的危險、幾乎沒有生產能力的采集狩獵生活時,他們已經穿戴著手織植物纖維布做成的衣服、佩戴著骨蚌等飾品體態豐盈地在田坊間勞作。在這一時期,他們走在了人類文明的最前沿。這個時候,他們走得穩健而幸福。
歷史在這里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然后又淹沒在更迅捷的發展變化中,漸漸被生活所覆蓋,漸漸為人們所遺忘。遺忘成為今天的一處遺址,一處廢墟。
然而,正如一位學者所說:沒有廢墟,就無所謂昨天,沒有昨天就無所謂今天生明天。廢墟是課本,讓我們把一門地理說成歷史;廢墟是進程,人生就是從舊的廢墟出發,走向新的廢墟。因此,廢墟是起點,廢墟是進程的長鏈。我們挾帶著廢墟走向現代,走向未來。
作者:張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