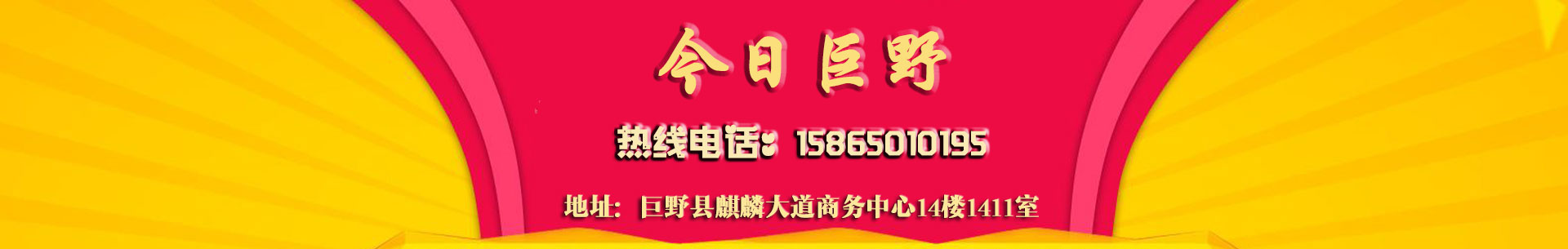
[晉]
王沈(生卒年不詳),字彥伯,高平(今山東巨野)人。西晉文學家。
王沈出身寒素,雖少有俊才,又不取與世沈浮的態(tài)度,遂為豪門所壓抑。仕郡文學掾,不盡得意,大概于晉武帝死后不久,“王政凌遲,官才失實”,即辭官歸隱,“還終于里閭”(《晉書·本傳》)。晉承襲并發(fā)展了曹魏的士族門制度,不用說似王沈一般的寒素之士,就是像左思,雖有貴嬪妹妹相撐持,亦感到沉重的壓抑,故而寫作《詠史》以抒懷。王沈歸隱以后,對于制度所造成的人才途路上的障礙,相比較而言較之左思還要清醒:“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于華屋,疏飯襲跡于耨耕。”士族制度本身只能是封建最高統(tǒng)治者與其相蔭襲的王公貴族,共同分享權(quán)利、財產(chǎn)、尊榮等方面的制度化、合法化而已;作為寒素之族只能在這種制度下被宰割被役使,“欲適煌煌之堂”,簡直就是癡想。何況制度本身所產(chǎn)生的弊端必然是:“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附形。”人才標準參照系的錯訛,價值觀念的本末倒置,必然滋生出更多的丑惡行為和丑惡的心態(tài),要保持人格的不扭曲,生于斯時則極為不易,何況還要以不扭曲的人格而“欲適煌煌之堂”就更不易了。因此王沈不僅以此繩己,還以此誘人而作《釋時論》。
《釋時論》仿對問體,設(shè)有冰之子發(fā)問,從常與非常提出許多詰難,而王沈以一個智者的面目予以辨解。其中心點則是,從一般難及個別,就必然生出眩惑;從正常推及不正常,就必然產(chǎn)生不解。就時間而論,對每個人都應是平等的;而就機遇而論,每個人的情況就會千差萬別。只有辨別時與時的不同,才能洞悉當今社會的訣竅;只有辨別時與機遇的不同,才能透徹人生的曲折。在王沈看來,只不過此一時彼一時,不能用常道來觀察非道,從一般論及個別。既然當今之世,“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凌云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guān)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眾途圮塞,捉足何錯!”從而渲瀉了他的憤激之情。王沈似乎在向有冰之子闡釋,實際上則是王沈自己所取的一條現(xiàn)實路線及自己所取這條路線的現(xiàn)實根據(jù)。
在晉,先是有劉毅用諫的形式表示了對士族制度的否定;后是左思用詩的形式表示了對士族制度的憤慨;而王沈是用論的形式提出了對士族制度的控訴。這足以說明王沈在當時所達到的認識高度及深度;由此可以確定王沈在思想認識史上和西晉文學史上的地位。至于稍后的松滋令吳郡蔡洪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嘆息”(《晉書》本傳),就更證明了這一點;再后來的干寶作《晉紀總論》,再次汲取王沈的意見,就又一次證明了這點。
王沈著作多佚,僅《晉書》存《釋時論》。

